
李樯在《黄金时代》威尼斯发布会现场
“能不能这样说,敢这样写剧本,因为你是李樯?”记者提出的这个观点立马被李樯反驳。他说,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自己依旧经历了新编剧会经历的那些事情,比如没有署名、当枪手、写完不给钱、用了你不承认……全都碰见过。“是我的人生观决定了我用这个结构,而不是想写一个先锋的电影。”
记者:许鞍华导演是一个作者性比较强的导演,您也是一个对剧本还原度比较强的编剧,这样的合作下,在现场是怎么协调配合的呢?
李:首先你看到的剧本是已经定过稿的,定过稿的剧本已经是我们达成共识。也会有争论和矛盾的东西,但是经过调和之后,定稿已经包含了我们共同的默契。最终剧本的完成时综合和各个的意见之后我自己来定稿。定稿之后就不希望把改剧本放到拍摄当中,我觉得要是这样要编剧干嘛?编剧要在开拍之后很踏实的完成之前设想的东西,而不是现场进行改,反正这是我跟其他导演合作的习惯,就是最好把剧本在拍摄前做的非常完备,所以你当然可以说是还原,但也是一个共同建设的东西。
记者:电影中有间离效果的东西,但是看过之后发现间离效果是选择性的,其实像萧红和萧军两个人很少站出来说话的。为什么让萧红站出来说话的部分少,是怕打扰到观众对这个角色的?
李:那倒也是不是,这是个相对主义的东西。第一幕萧红对着镜头说我叫张乃莹,那已经是非常超现实主义的了,应经非常破坏电影的讲究性了,那就足够了。包括她死的时候是盯着镜头死的,这个其实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里面的间离并不是针对萧红和萧军,而是针对历史观和人无关,历史不可能复原。这个间离是希望客观和主观能够平衡的交融,而不是提倡你的个人性。其实人是最复杂的宇宙,是很难被琢磨的。其实电影中的台词都是她的作品,我看到一个影评在骂说,都不写她的作品,我说你要是读一点萧红你就会知道通篇都是她的作品。包括东北的整个部分就是《商市街》,包括另一个影评人在骂说“死之前才让萧红回忆她的《呼兰河传》”,他知不知道她死的那天才写完啊。当然这样的电影很难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拍“李白传”“毛泽东传”“鲁迅传”是相当难的,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心灵就有千千万万个作者。所以我觉得对一个电影的接受度,应该是抱着探宝的感觉,是收获的感觉,而不是直接的我认为宝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不要抱着极端的想法,先听听别人是怎么处理的。
记者:您说每个人对人物的理解都不同,那您跟许鞍华导演在创作上对萧红的理解有没有分歧的时候。
李:当然会有各自的理解。比如说萧红是真的热爱爱情的,还是在爱情中历练?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她身受凄苦,一次次飞蛾扑火。是为了写作而这样还是因为这样而写作。一千万年萧红都说不清楚。
记者:您个人对她的理解是怎样的?
李:我个人肯定对她有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愿意把我个人的理解带到荧幕上。这是一个公共的殿堂,可以有我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不能打造一个我李樯理解的萧红,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越来越不愿意主观,因为我觉得那样我会越来越没有自我。对萧红,我觉得喜欢她不喜欢她,有意思的东西都分外珍贵。就像一个人的遗物,不管有没有用,我都放在那,用来证明他曾经肉身存在的痕迹。
记者:从我知道这个片子要拍,到我看到这个片子,我脑海中一直萦绕三个字就是:实验性!无论您写这个片子的时间长度,这个片子的时间长度,还有这个片子的类型,容纳的所有的明星的强度,我觉得已经上升到一个行为艺术的程度了。
李:我觉得不是行为艺术。最起码,当我和导演在做萧红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可以把萧红换成别的人,我的兴趣是如何做一个“人”,萧红是个题材和载体。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义务去探索一下不同的写作方法。可能过程是艰辛的,结果也不可知,但是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看待历史,看待人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写剧本的过程中也教育了我自己。
记者:您说教育了自己,教育的内容是?是剧的方向?
李:比如我对人物的思考,对讲述人的时空的思考,认识真的活在一个时空里面的吗?我跟他在同一个时空里,他讲述的都是他记忆中的事情。所以电影中有很多超时空的东西,我觉得人永远是活在过去、未来、当下的,是我们划分了物理世界。包括你如何确定你认识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偏狭的事情。你可以强调你的感受,但是你的感受只是你的。
记者:在拍摄时的素材大概是多多,是怎么选取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看到电影中的为人交往就是吃饭聊天喝酒,下一场又交往到一定程度吃饭聊天喝酒。
李:就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领略的问题,我们容易对一个时代或一个人产生主观的想象。这个是一个人的权利,想象力也很珍贵,但是你真的深入到那个时代,比如你看鲁迅他一生的日记,没有轰轰烈烈高起高打的举动,人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流逝了,人的渺小与伟大也产生于此。并不是每个传奇人物都生活在动荡、浩荡的伟卷之中。人的一生除非碰到战乱,不都是在饮食男女、日常烟火中流逝的吗?但你的心是深不可测的。
搜狐娱乐:我本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会不会太大胆,因为观众看了三个小时没看到一个戏剧性的高潮。
李:电影有很多种,老说观众,观众代表着谁,观众有医生、有律师、有农民工、有环卫工人。有太多人,我们老说为观众,观众太丰富了。我觉得很多常识性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就像艺术上的每个流派,并不是强制性的流传下来的。我只是质疑观众这两个字代表的含义和身份。
记者:我想问一句话,不知道您同不同意,敢这样写剧本是因为您是李樯
李:不是,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写他心目中东西。我们找钱的过程很难,不是因为是许鞍华和我就很容易,前前后后很多年都不要投,我面临的处境好新的编剧一样。所有编剧经历过的事情我都经历了,没有署名、当枪手、写完不给钱、用了你不承认……全都碰见过。我们面临的处境是一摸一样的。是我的人生观决定了我用这个结构,而不是想写一个先锋的电影。是我的人生态度决定了,而不是为了表现我是谁谁谁,我真不敢,对于写作我还是胆怯的。因为我觉得作家编剧跟演员还是不一样,你这一部成了,下一部的百分比还是零。
记者: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太任性了,我担心它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表达
李:你可以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个人任性的标准又不一样。我觉得我是太不任性了才会这么写。比如我可以写萧红对于爱情是非常执着和贪婪的,我可以写萧红有可能是情欲是很旺盛的,我可以写爱情对于萧红来说只是作为作家哺育她的工具,我没有这么去写,我觉得不叫任性,我觉得任何一种过于强烈的态度才叫任性,而不是说当我客观起来了才叫任性。我觉得每个人对电影有读解我都很高兴,我觉得一个电影成功就是一个公共的建筑,每个人都可以指点江山。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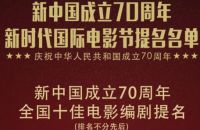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