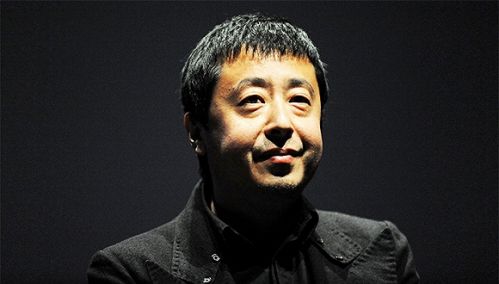
导演贾樟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展开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线,来表达我对情感、对爱的理解”
记者:拍摄《山河故人》的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在拍摄完《天注定》后,我就想拍摄一部专注于情感的影片。虽然《天注定》中也有情感的表达,但更多是专注于暴力和社会的变动,社会问题带给个体的危机。
在我的电影中,我从不会单纯去拍社会问题,因为我不是记者也不是社会学家。我所感兴趣的是社会中的人。当然,我不会把社会本身和作为个体的人切断,但我电影中的叙事焦点绝对都在人的身上。
《天注定》的叙事焦点在人的生存危机上,一个人,因为他所遭遇的暴力,他可能会从一个弱者和暴力的受害者转变成暴力的实施者,这种转变是触目惊心又铭心刻骨的。而在《山河故人》中,我想表达的是近些年来,我们很多的选择、价值观、新的科技和生活方式给情感带来的巨大改变。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满脑子想的可能都是谈恋爱吧,那时候,生命中仿佛都是爱情,那时候,你不可能会去想,人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只能等时间来告诉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会从恋爱的状态转换到成立家庭,还需要去面对逐渐老去的父母,尤其是到了四十岁之后,生命中的很多事情都向你展开了,在此之前,它们都是躲藏着的。
人生中的生、老、病、死,都伴随着爱。而我觉得,爱,就像修行一样,都需要伴随着漫长的时间来进行体会和感悟,在《山河故人》中,我展开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线,来表达我对情感、对爱的理解。
记者:为什么会给影片设置三段式的形式?最后一段关于未来的想象又是基于怎样的现实基础而展开?
贾樟柯:我最初写剧本的时候,并没有想把故事延展到未来。但是写着写着,我总会想,电影中那个孩子的将来会怎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被父母的选择所决定的人。他母亲,一生中面临了两次选择,一次是结婚,她很理智地选择了拥有财富的人。另一次选择是离婚,她选择让孩子的父亲来抚养孩子,因为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风投家,积累了很多财富,她的理由是,财富可以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但其实对她而言,这是一种牺牲式的选择。
电影中的孩子很被动,他就这样被父母的选择决定了以后的命运。所以当我写完当代部分之后,我觉得应该继续往下写,写到未来,看看这个孩子以后会怎样。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未来可以有大胆的设想,而不是仅仅基于现实存在所提供的依据。
我并不把《山河故人》看做三段体的电影,我更喜欢把它说成是人生的三个阶段,里面有两代人在叙述焦点上的交替。
我觉得,把情感和时光放在一起,是一件挺美的事情。
记者:通过《山河故人》,你是不是还想传递一些社会意义层面的思考?
贾樟柯:在目前中国的情况和体制之下,虽然有些人拥有很多财富,但其实大家的命运都挺像的。我记得之前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不太喜欢别人把我所拍摄的对象形容为底层人,我更希望他们被称为是非权力拥有者,而这个非权力拥有者涉及面非常广,人群非常大。不是说你拥有了财富就拥有了权力,今天你是一个老板,非常有钱,但明天可能随时就完蛋了,在权力之外,大家的生存境遇其实都挺像的。
前一阵,天津的爆炸事件,我上网,看一个网友说得特别好,他说,买万科房子的那些白领和中产阶级,在这之前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得自己这一生会和访民构成联系,然而房子一炸,他们瞬间就变成了访民。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这种感觉就是《山河故人》想表达的。
“我觉得要忠实于自己对于当下中国的感受”
记者:很多影评人,尤其是西方影评人,对于你的电影,他们都发出过类似“透过贾樟柯的电影,读懂中国”的评论,你怎么看待这些评论?
贾樟柯:我没有任何责任去讲述一个国家的命运。
法国影评人让-米歇尔·傅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有贾樟柯这样一个叙述者,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但对我来说,在创作的时候,不会把初衷和主旨拔高到“讲述国家命运”这么宏大的命题上。你很难用一部影片来对一个国家做一个完整的描述,事实上,这也不是一个艺术家需要去做的事情。中国变化这么快,在这飞速的变化中,社会中每个个体所遭受的情感和生存危机,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也是我愿意去记录和表达的。
另外一方面,在我的电影中,我谈的都是当代的故事,我觉得要忠实于自己对于当下中国的感受。可能我一直反应比较快,只要在现实生活中让我有所感触的,我不会拖延,我会马上去拍出来。
在我刚从事电影行业的时候,基于自己长期以来对中国电影的观察,我发现电影里所表现的东西与这个国家真实生活的人好像没啥关系。说难听点,那样的电影就是废物。多少年后我们再回头看,没有人真的认为那时候的人是那样生活的。当然这样的感触并不直接构成我拍电影的初衷,只是某种诱因。
记者:在《山河故人》中,你对于人生的选择、亲情、沟通等命题都做了诠释和解读,广义而言,你认为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终极命运是什么?
贾樟柯:孤独。
我一直在想,电影中的涛,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她会不会有新的感情?促使我想到这点的是我父母的遭遇。
我的父母非常恩爱,然后我父亲在2006年突然走了,从此之后,我觉得我妈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因为她相爱的人走了,我们儿女是永远取代不了的。妈妈现在跟我住,每天见两面,早上和晚上,那么,中间那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她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也没人陪她,如果我父亲在,他们是一块儿的,会一起做这个做那个。
从此我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避免不了孤苦,总有一个人要先离开。虽然这些事情现在距离我还比较远,但是一想到就会很难过。
记者:能谈谈你拍广告的事情吗?
贾樟柯:广告的操作与电影不一样,广告的拍摄是有严格的程序,一般来说,我们作为制作公司是不应该参与创意的,一般是广告公司来进行创意,我们制作负责完成拍摄。因为一般来说,是广告公司更理解品牌的需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么一个广告,这个产品的需求是什么,它所产生的目的是什么,它要传达给受众的是什么观念,谁是它的受众,这些都需要很严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分析。
但是这几年,却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公司跟广告公司一起来找我,他们告诉我大概需要怎样,然后你来随心所欲地提供创意,这样的广告对于我来说,可以有很多的自我空间来把握,我也可以把我的偏好投射在里面。比如我最新拍摄的“陌陌”的广告,表现那种年轻人由网络而来的聚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里面有好多我之前生活中感受深刻的“点”。比如我们现在有人在网上约“比武”,真的是学习武术的年轻人或者武术爱好者来进行切磋,比如怎么理解形意拳,然后约好之后,某个下午,到某个人家,约好之后大家就开练,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山西古塔保护的项目,若干年前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消息,邀请我参加,我没时间,但这个事情我一直记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特别美,大家一起约好,去寻找那些被人遗忘的古塔,把它拍下来,记录下来,保护它所以我在广告中把这些“点”都融入了进去,我想我拍的广告其实都带有些许贾樟柯独特的味道。
“我现在在刻意保留实体情感,避免自己变为信息的终端”
记者:除了电影和工作之外,你的日常生活一般怎样度过?听说你还在山西开了一家小面馆?
贾樟柯:生活中不能只有电影。
有段时间,我发现,我所有的活动、见的人、做的事情,都是与电影有关,这让我觉得很“变态”,仿佛一个人彻底变成了电影的奴隶,这是不对的,我需要去寻找一种电影之外的生活。
我在山西开的面馆其实是带有俱乐部的性质,不对外营业,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场所,让我把电影丢在一边,在那里和小时候的朋友、同学见面,八卦、扯皮、聊过去的事情,这让我觉得很快乐。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更年轻的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终端,不停地接收外界砸给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还有大量的slogan(口号)。但事实上,网络化的信息逐渐入侵了我们的生活,实体的情感体验越来越少,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你会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个概念和口号里面。所以我现在在刻意保留实体情感,方式就是尽量抽出时间和老朋友聚会、聊天,大家一起跑步,避免自己变成信息的终端。
记者:作为一个创作者,你通常的态度是面对观众还是背对观众?换句话说,你在乎别人的评论和看法吗?
贾樟柯:我拍电影是因为我有着很强烈的诉说欲望和沟通欲望,虽然听我诉说的人是谁,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保持我的热情。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介,我拍电影也是想把自己的情感世界分享给别人。
但是,期待沟通不等于迎合和取悦,迎合观众和取悦观众、与观众沟通是两码事。拍电影难免会被各种角度的评论所纠缠,我觉得要学会和它们相处。如果别人说得对,你会明白他说得对,说得不对,也不要被干扰。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屏蔽不了评论,因为你总会使用网络工具,你要用微信、微博,也许你不想看,但最后总能看到。但佛教里不是讲“不辩”嘛,所以我没有必要为它们所改变。
记者:你的电影一直在关注现实生活,但之前你在演讲中仿佛也提到过,觉得中国电影的市井传统丧失得很厉害?
贾樟柯:其实现在好一点了,但这种传统依旧被中断得很厉害。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1949年之前,中国人是属于家族与地域的,但1949年之后,我们更讲究组织。组织其实更是一个动词,比方说,党是一个组织,工会是一个组织,共青团是一个组织,然后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组织。人的聚合从村落、家族、街道变成了单位化,那么在组织的过程中,人的单位属性就产生了变化,所以在这种组织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革命文艺的理念,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的文艺已经在美学上把市井这一块彻底忽略掉了。
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有一部我很喜欢,是张泽鸣的《绝响》。他在广东拍的,在那里,中国电影似乎又隐约回到了市井中去,但那种感觉不强烈,显得很孤独。直到后来我在电影学院看了《马路天使》,我觉得这才是对中国日常市井生活准确而活泼的描绘,尔冬升的《新不了情》就继承了《马路天使》的传统,拍得非常有味道。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文化断裂的后遗症。
记者:这样听上去,你似乎是一个怀旧的人。我们在你的工作室看到很多之前电影的胶片,你留恋电影的胶片时代吗?
贾樟柯:我不怀念胶片。
现在凡是胶片能够达到的效果数码都能做到,人们对于胶片的怀恋,其实更像是一种惯性与恋物。
电影从业者对于胶片的坚持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接触了数码,你会发现它会帮助你完成得更好。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最高端的数码摄影机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已经完全可以覆盖胶片,甚至超越它。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