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郊区的鸟》剧照
27日晚,第12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终于落下帷幕。仇晟导演的《郊区的鸟》不负众望获得最佳剧情片,呼声最高的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获得最佳纪录片,古涛导演的《驯马》荣获了最佳艺术探索奖。

此外,拉华加导演以视角纯真的《旺扎的雨靴》赢得最佳导演,池韵则凭借《美丽》中充满个人魅力的表演获得最佳演员。

FIRST竞赛获奖影片名单
我们今天要重点推荐的,便是荣获最佳剧情片的《郊区的鸟》。当仇晟导演激动地许鞍华和苏照彬两位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时说:“把我的电影献给所有爱自由的人。”作为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大热的影片,仇晟导演无疑交出了一份让人侧目的答卷。
影片《郊区的鸟》在结构和表达上都展示出大部分青年电影所没有的锐气,初出茅庐就敢在结构上如此大胆,并在影像风格上对各家经验消化、借鉴,是非常难得的。尽管技术手法上还有些许不够成熟之处,但仇晟导演在形式上的野心和冲劲可见一斑。

有人说《郊区的鸟》的复杂程度不亚于《路边野餐》。影片中一共出现两次片头,以时代变迁为大背景,在三个重叠交错的时空架构起整条叙事线,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换个说法,我更喜欢用少年初成-方出茅庐-成熟之后。这三个看似连贯的阶段,却被导演用抽象的片段式时空打断,彼此人物镜像对应但并不相连。
少年夏昊仿佛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夏昊的小学时代,影片的前100分钟里,观众都被带入少年-青年双线平行叙事的陷阱中。青年夏昊毕业后在社会中爬摸打滚,对过去已经记忆模糊,冥冥中遇上的女友燕子,同样失意于人生的同事,老油条的“差不多”上司,每一个过去缺失的灵魂都在现实的浓霾中努力挣扎呼吸。

毋庸置疑,《郊区的鸟》中最让人沉浸在影片叙事中的就是少年时的学校时光,大伙儿踏青时捅过的鸟窝,一起在被窝打过飞机的好基友,充满仪式感的道别,动物园中的暧昧拥抱,旧楼间玩过的组队野战射击,一起奔跑过的足球场,情窦初开的约会和表白,蒙太奇流畅且梦幻地呈现这一段时光的美好。
直到影片用隐藏的线索暗示小胖的消失,当老师让同学们画一幅未来的城市,每个小伙伴的画作都意有所指,婷婷画的高楼大厦,夏昊画的新型列车等等,唯有小胖的画作是一幅混沌的“意识流”,喻示其消失在时空中的未来。在寻找小胖的旅程中,经过拆迁区,坐上废弃的公交车,跨过铁轨,趟过河,翻过墙,曾经一起嬉闹的孩子们,在经历中一个个掉了队。

影片到最终都没有告诉大家小胖消失的原因,搬家了?生病了?那么其他人呢,他们的再见又是为何。到最后,看看自己,每个人生命里不也曾有过这样一群渐渐掉队的小伙伴吗,我们曾经的住所有多少也成了现在的拆迁区?成年后的夏昊记不起少年时经历的一切,是不是当童年的环境消失后,记忆也会随之消失?
少年与青年两条叙事线各自运行、偶有交错,但不时出现的叙事偏差似乎又在隐约地暗示。影片不仅仅是现实与过往的交错叙事,在郊区为隧道测绘的研究小组与河边废墟寻找消失小伙伴的少年们,到底是各自时空里的诡秘人生旅程,还是以日记为线索相互勾织拼凑出的完整人生,抑或这只是青年夏昊在生活困境中想象出来的奇幻童年?

直到第二个片头出现的时候,导演才给出明确的暗示。影片进行将近100分钟后,出现第二次片头,似乎这个时候的夏昊又开始了一段相异的人生。与庸庸碌碌的青年夏昊相比,第三层空间的成熟夏昊自由地在林中与同伴寻找乌托邦中的蓝鸟,望远镜中隔着时空观望到的少年踏青,到底是虚幻还是平行时空,影片把解答机会留给观众。
导演在三个时空的出现与消失,用了“地面沉降”这一概念。当少年夏昊的童年乐园随着拆迁消失在地面,当玩伴们一个个走失在命运的旅途,少年夏昊的“地面”沉降到时空之外;当青年夏昊所探测的隧道真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渗水区时,他与他的“地面”也随之沉降到时空之外;最后出现在第三时空夏昊,却与“测量师夏昊”的同事结伴郊外寻找蓝鸟,在望远镜中窥见少年。

影片中用鸟蛋、日记本、口香糖、望远镜、蓝鸟、谜语等意象作为无限时空中的相交奇点,连接其这三个独立时空中的命运共通点,让人不禁在想,平行时空中的“我”也许命运不同,但是否吃着同一片披萨,嗅过同一朵花,喜欢过同一个人。
在映后的对谈中,导演曾谈及夏昊的职业设定,的确是参考了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土地测量员一职。卡夫卡的《城堡》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似乎那位“预备测量员”永远在城堡的外围一无所成地忙碌“转正”。

也许很多读者都会遗憾《城堡》是一个没来得及完结的小说,但换个角度想,《城堡》会有完结的一天吗?答案是不会,转正了又能如何?《郊区的鸟》中的正式测量员夏昊同样要面对这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裙带关系、官僚主义敷衍了事。导演在处理少年夏昊与青年夏昊这两条主线的时候,让少年时期的“虚”更加梦幻而轻盈,而青年夏昊的“实”显得更加拳拳到肉。
美中不足在于,影片中有两点瑕疵。一是在青年测绘师夏昊部分的章节,过多地使用推拉镜头和快速变焦让人看得有点难受。洪尚秀的快速变焦多数是为了突出人物与环境的对峙状态,但《郊区的鸟》更多是单纯概念性镜头,不承担叙事作用。其次是成人演员的表演不够尽如人意。相比之下,少年部分小演员们的表演更显得灵气十足。

尽管如此,《郊区的鸟》在整体创作上依旧可圈可点。创作者在作品的解读上用了非常讨巧的开放式解释,其聪明之处在于将解答空间完全甩给观众。这种片段式的叙事线每一个段落都似是而非,欲拒还迎地透露着半真半假的信息,无论怎么解答似乎都能说得通;观众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编织故事,也不失为一种新鲜的尝试。
独家专访仇晟导演
记者:片名为何叫《郊区的鸟》?
仇晟:因为我最先想到影片的结尾,就是夏昊在密林里面寻找一种鸟,当时就想到《郊区的鸟》这个片名。郊区的鸟的状态比较像影片里人的状态,就是也不在城里,也不在乡村,飞来飞去种很焦虑,无处皈依。

记者:影片为何会采用4:3的画幅,是个人美学诉求吗?
仇晟:因为我之前在FIRST训练营拍过个短片《雷电》,然后就一直在研究4:3。就感觉看一个4:3的画幅,你会比较觉得,这个画面是个物件,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它是一个明信片,或者是实在的可以触摸的东西。反之宽荧幕的画面,则像是你在看导演的视野或者摄影师的视野。相比之下,宽银幕的故事会更加强制性,而4:3跟观众的距离则是比较松散的关系,观众可以稍微抽离一点,比较符合《郊区的鸟》。
记者:你说“土地测量员”的人物设定灵感来自于卡夫卡的小说《城堡》,那影片主旨与卡夫卡有共通之处吗?
仇晟:对,我一直很受卡夫卡小说的影响,我觉得他描述的主人公,不管是K还有其他主人公的状态,都跟我有挺大共鸣。卡夫卡说过,巴尔扎克手杖上刻着“我能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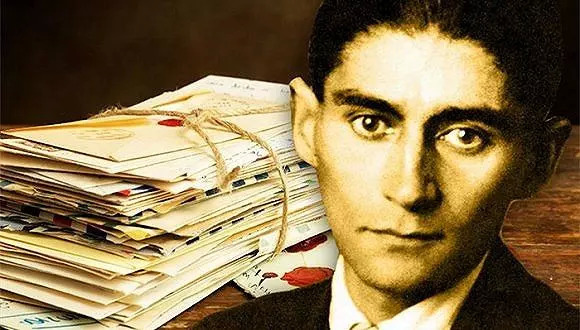
其实对于夏昊,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就是时常感觉,一切障碍都摧毁了我,无论从工作上,从情感上,还有从城市空间上。我觉得K和夏昊的共同点就是,在城市空间里面他们都时时刻刻感受到压迫。无论空旷的空间,或者密闭的空间,对于夏昊来说,都会造成精神上的折磨和影响。所以卡夫卡有时候也是一个特别的神秘主义者,他那种精神上的折磨和影响,都是很理性地慢慢施加到主人公身上,这个部分我很认同,并且也深有感受。
记者:中途为何安排测量员集体进入仪式感的沉睡,才让孩子与成人两条线产生交织?是有两个时空维度吗?
仇晟:这是很关键的一场戏。那天其实还挺巧的,在拍的时候,机器出了问题,从早上11点开始机器就坏了,一直修不好,没办法,只能再从别的地方调一台过来。于是几个演员在那没什么事做,他们就靠在河堤边睡觉,然后我觉得,这就像是一种时间的暂停,或者说是一个陷入,好像突然中了蛊的那种状态。由此激发灵感,我就设计让小孩进入这个空间,就有了粘泡泡糖这个动作。

记者:影片中有很多废墟场景,让我想起这些年贯穿南方的拆迁,我们的童年秘密基地空间被不断压缩。身为杭州人,你有在影片中融入类似感受吗?
仇晟:影片中有很多拆了一半的楼,也有所谓的地面沉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意外的拆迁。我自己童年生长的区域,杭州的火车东站附近,同时也是运河流过的地方,我们的地方就被拆得支离破碎。因为原来是一个比较有机的社区,就是大家互相之间有那种社区感,我们会有小区的一个商店,它可能是人们交谈和议论的地方,以及我们可能坐在门口晒太阳或者吃西瓜,这都是大家可以议论或者交流的。但现在这些空间全没了,就变得特别规整,不再有那种开放的可以交流的空间。
记者:摄影有很多透过望远镜观察世界的圆形构图,这里有模拟鸟类视角的想法吗?
仇晟:圆形构图既是望远镜的视野,看上去又像是鸟的视觉,因为它凑得特别近,又是圆形的状态。但它不一定是所谓的主观镜头,它更像是一个第三者,或者一个鸟类视角,也可以说是一个上帝视角。

记者:常有导演说,孩子是最难拍的,更何况还是一大群孩子,你是如何调度他们演戏的?
仇晟:其实相对来说,一大群孩子比一个孩子好拍点。在拍之前,我先让他们形成我想要的人物关系,就是给他们做一些训练,让他们一起做些事情,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搭人梯,帮他们互相构建关系。然后拍的时候,就是群戏部分,适当给他们一些刺激,或者激起一个话题让他们去讨论,这时候就会自然地走向我们想要的那个情景。反而是小孩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特别多的可互动的东西,专注力也不是特别高,这个时候就更要想办法去刺激他,跟他讲情感,给他一个比喻,或者让他去关注其他的东西来达到满意的效果。
记者:影片中那些琐碎有趣的细节,有多少来自于你的童年生命体验?比如剪头发那场戏让我印象很深刻。
仇晟:最开始的远征部分,有很多来自我的个人生命体验。远征部分那种一个一个掉队、最后停下来的感觉,那些人物也都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都来自于我的生命体验。而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应该说有一大半还是后来创造出来的,就是结合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做的设计。剪头发这场戏,我是想说,到底一男一女两人怎么走到一起,就是“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那种感觉。当时这场戏写完后,我制片人给他一个朋友看,然后那个朋友说,他小时候有个女孩对他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我还蛮惊喜的,尽管这纯粹是我编的。

记者:为何会选择李淳和黄璐来主演大人的部分,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吸引你?
仇晟:李淳是因为我跟他聊的很好,我刚开始会担心他长年在美国,可能不太合适这个角色。但我跟他聊完后,发现他对剧本理解很深。包括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讲,他觉得剧本讲的是宇宙的平衡,就是说此处失去了在彼处会得到,彼处失去的在此处会得到。他跟我讲,最后地铁隧道的部分,让他想到了柏拉图的洞穴理论,那几个人可能始终是在地下,可能从来没看到过真正的鸟,我觉得他理解还蛮深的。然后就是他的气质跟我想要的夏昊的气质也接近,就选用了他。黄璐的话我倒没有跟她那么多地聊剧本,我主要是看她之前的一些作品,像《推拿》《云的模样》还有《中国姑娘》,我都挺喜欢的。

记者:影片中多次出现快速推拉镜头,很多影迷就此想到洪常秀导演,有致敬意味吗?
仇晟:其实推拉的镜头,跟洪常秀还有另一个导演叫小克莱伯·门多萨,都有关系。他们两个人的推拉镜头性质也是不太一样,洪常秀是那种修辞型的推拉,就是加一些语气助词;小克莱伯的推拉则是比较有时空感的的推拉。回忆的凝视或者郊区的空间,两方面都有采用。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4:3的画幅,其实就会形成比较奇怪的组合,但正是我想要的。
记者:你本身也是很资深的影迷,你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受过他的影响?本片的很多场景其实有着台湾或日本电影的味道。
仇晟:侯孝贤、蔡明亮、洪常秀等等,我说的可能都是对我比较近的影响,还有布鲁诺·杜蒙、米格尔·戈麦斯,对我近期的创作影响比较大。

记者:影片的音效和配乐很有灵性,可以谈谈吗?
仇晟:昨天的场次,音效效果其实很差,所以很多细节还是没有出来。我是想让环境应用的那种音效也成为对话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表意的工具,比如说我会在他们两个在床上耳鬓厮磨的时候,加入一些打桩机的声音,其实就是给那种情爱加入一点压抑和恐怖的气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感受。童年部分的话,会特别强调环境中的虫鸣鸟叫。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是人为的发声,一个是自然的发声,是不一样的声音氛围。
然后音乐方面,我其实跟小河做了特别多版的修改。最开始小河老师喜欢童年的部分,他给童年做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但后来我基本把它拿掉了,因为我觉得不想让童年部分太甜美。我想说,童年部分也是长大在那种忧郁跟甜美之间摇摆的状态。后来其实我们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电子化的比较都市的声音,整体的音乐有点侵略性或者有点都市化。然后小河也做了首片尾曲,中间也有一首摇滚乐,那两首歌都是比较重的。

记者:影片结尾发生于树林中,李淳他们如梦初醒般听到远处孩子们的声音。这个结尾有何寓意吗?为何选择在这里结尾?
仇晟:其实结尾这个看到孩子的瞬间,可以是久别后的重逢,也可以是初遇。所以这场戏既是结束,也是开始。
记者:这几年,看到越来越多南方系电影开始冒头。你未来的创作会一如既往围绕南方吗?
仇晟:反正我下部片还是想在南方拍,还是在杭州拍,因为我觉得杭州还有些东西没有被我探索完的,再之后我也还不太确定。同时,我也有在写小说,准备出一个短篇集,集名就叫《湿地》,里面会出现重要的南方元素,包括水,我觉得它是情欲、感情,也是记忆的流动。

独家专访演员邓竞
记者:作为《郊区的鸟》中蚂蚁一角的饰演者,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获得这个角色?
邓竞:去年六月份毕业回国的时候,一直在寻找机会,也是无意间,当时并没觉得自己能够往文艺片方向发展。但是机缘巧合看到了那个组讯,然后想着锻炼一下就去了仇晟他们那个电影公司,去面试了两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喜欢大卫·芬奇之类的导演。另外我喜欢的音乐人,他也是很喜欢的,所以感觉很聊得来。蚂蚁这个角色,反而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

记者:对于土地测量员这个冷门职业,你个人有着怎样的理解?
邓竞: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蚂蚁是一个普通工人。但拿到角色之后,我有去思考他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碰巧我的表哥学的是地质勘察,我就从表哥开始去了解,说在工地里面他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自己也去工地观察过一段时间,他们生活的状态和使用器械的方式,以及生活习惯。
记者:拍摄期间,与李淳、黄璐等演员相处如何?跟他们演对手戏,有什么感触?
邓竞:相处很好,我们现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李淳在台湾可能赶不过来,但我们私下都有联系。黄璐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上次还参加了她的婚礼。定了角色之后,导演会带着我们几个演员去玩密室逃脱,或者去酒吧喝酒,去交流一些除电影以外的事情。

跟李淳演对手戏,可以说越来越有默契吧。我之前有在他爸爸作品里见到过他的样子,现实中他这个人也是非常随和,在剧组除了和导演以外,跟他的交流是最多的,我们平时生活也会在一起吃饭,他也会问我对于他的角色和表演的一些看法。
记者:在建立角色的过程中,与仇晟导演是如何进行日常沟通的?他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比如让你去看某部电影之类。
邓竞:有的,因为这是我第一部电影,对剧组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不太了解,一开始导演看我表演有问题的时候,会让我先从模仿某一个具体的角色开始,后面再让我自由发挥,是这样一个过程,给我的空间会大一点。

记者:蚂蚁这个角色,表演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邓竞:我觉得动作部分其实并不难,就是模仿一个工人的状态,难在他的心理状态。蚂蚁在电影里面的心理状态是有蛮多变化的,虽然他不是男主角。然后要给观众,通过我的动作和表演来呈现这种状态,这是比较难的地方。
我觉得你演任何一个角色,都能够在角色里面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相似的一些地方,不一定是完全相似,但你只要把共同的地方找出来,然后再通过自己的想象和一些剧本内容,把它构思出来,来完成这样一个形象。

记者:你之前有在国外求学的经历,对于表演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在你看来,国内外演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邓竞:表演这东西要想站得住脚,就是在我理解的情况下,不是一个老师能够决定的,是众多的观众和你自己来决定的。在国外的话,表演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对一个表演的评价,你是要得到所有观众、老师和学生的一个反馈的,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全面理解这个角色。
国内的演员非常重视基本功,所谓的基本功就是说身形表,以及一个人的台词功底、肢体动作和气息,他们都有很高的要求,基本功非常扎实。但是我觉得在国外学表演,你的空间会更大,你重视的会更在于角色的灵魂。

记者:在《郊区的鸟》之后,你目前还有参与别的电影项目吗?在创作上未来有什么打算?
邓竞:在去年拍完《郊区的鸟》之后,还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四零四》,也是一部文艺片,饰演的男主角。未来的话,各种角色我都愿意去尝试,因为电影的空间我觉得是无限的,就像每个人的想象无穷无尽,可以做更多尝试。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