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
是学雷锋纪念日。
是周总理的诞辰。
巧了的是,今年的3月5日,也是现代著名作家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
更巧了的是,今年的3月5日,也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
古人云:“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盛于立春,衰于惊蛰。”,惊蛰过后,地气开始上升,春暖花开的日子就要来了,那么战胜疫情的日子也很快就要来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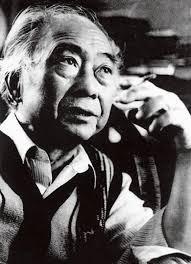
汪曾祺老先生,大多数的中国人应该不会陌生,多多少少肯定读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有好几篇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
笔者第一次读汪老的文章,自然也是初中的那篇课文—《端午的鸭蛋》,只不过那时候好像很傻不太能体会汪老内心的某种情结。
后来也没有再读过这篇文章,可就是初中的这点的记忆,还是让我深深的记住了高邮咸鸭蛋。
几年之前,我在苏州上班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一年的端午节单位中午加餐不仅有粽子,还有咸鸭蛋,这就一下子让我想起了《端午的鸭蛋》。

我拿到咸鸭蛋之后,也忘记了汪老描述的吃法,照着吃鸡蛋的法子,在桌子上磕破皮,就剥着吃,咬了一口蛋白还能接受,再吃蛋黄就着实太咸了,还是有一点接受不了,这可能就是我个人口味的问题,毕竟作为一个北方人,打小不太怎么吃鸭蛋。
说起汪老的文学作品,怎么也不可能饶过那篇不朽的《受戒》,当年在语文读本上读到之后,心一下就被软化了。
我现在根本记不清,高中那会到底读了多少遍《受戒》,总之就是喜欢这篇小说,爱不释手,一生的收藏。

当年读《受戒》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的就是享受,就是美好,简直就是如沐春风的感觉。
清新自然的文笔,朦朦胧胧的爱情,根本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在讲少男少女的生活,讲着讲着两个就心意相通了。
那种原生态的感情质朴自然,天真无邪。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受戒》有神韵,有意境美,字里行间能够传达出情绪,读者能够读出对生活的热爱和美好人性的无限赞美。
电影是视听艺术,但是本质上应该是更靠近叙事的艺术,没有故事文本的电影要么就是纪录片,要么就是没有灵魂的现代光影技术。
在电影文本的写作上,少不了文学性这么一说,这个文学性是什么,应该是意境美,应该是神韵,应该是情绪表达。
《受戒》作为一篇小说,故事情节极简,结构也很单一,但是仍然完成了艺术的表达。
有的电影也不注重故事情节,也依然能够完成艺术的表达,比如侯麦的电影,侯孝贤的电影,洪尚秀的电影,是枝裕和的电影。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受戒》作为小说和当今世界上的某些艺术电影,在意境的塑造上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和《受戒》同样,在意境美的塑造上能和艺术电影相比,还有一篇现代名作,这就是沈从文的《边城》。

汪曾祺老先生写小说写出了不朽的《受戒》,写散文也是一等一的高手,那些平淡质朴,悠闲自在的文章,也是当代人的心头好。
他写的那些关于美食的文章,到现在仍然是很多吃货心中的美食指南,他除了写故乡高邮的咸鸭蛋,还写黄油烙饼,还会写昆明的烧鸡。
他写吃西瓜,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清凉。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他还说。
“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咸北甜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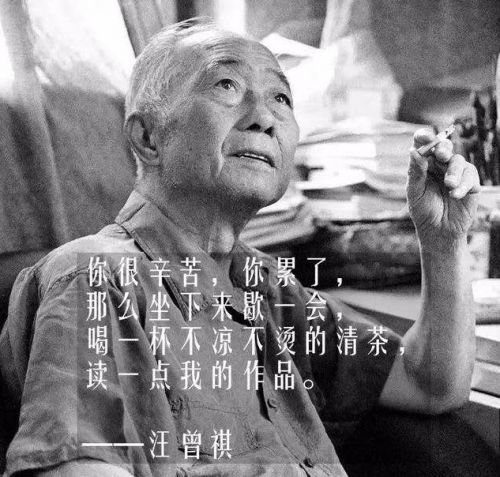
汪曾祺老先生出身在江南的读书人家,求学在西南联大,中年时期赶上了反右,赶上了文革。
在那个动荡年代,他依然凭借自己的博学多识,还是得到了某些当权者的青睐,被邀请去写样板戏的唱词。
这就是毛主席当年亲自拍板的《沙家浜》。
一个作家,被后世铭记,一定是因为他的作品,我们后辈读了这些作品,多多少少对自己的人生会有点影响,故我们纪念他。
《受戒》是不朽的。
创造她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朽的。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