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森特·马拉瓦尔,著名监制、发行人
曾任职UGC、StudioCanal等法国知名电影公司,2002年创办Wild Bunch,发行电影囊括八座金棕榈奖,堪称戛纳电影节常胜军;亲任监制超过五十部作品,包括戛纳金棕榈奖《我是布莱克》、《阿黛尔的生活》、威尼斯金狮奖《摔角王》等。热爱亚洲电影,曾监制陈果《榴梿飘飘》、娄烨《紫蝴蝶》等片,并经手发行众多亚洲电影至全球市场。亦与名导肯·洛奇、吉尔莫·德尔·托罗等长期合作,被誉为具有全球最强发行能力的制片人之一。
本文经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授权发布
Q:请问你通常是怎么看出一位短片导演的潜力?怎么看短片有潜力发展成长片?有什么特殊的欣赏角度吗?
文森特·马拉瓦尔 :对我来说,要有一定长度的短片才能去做评断,如果是一部只有一个概念的短片,很难去评断他的导演功力。
我的评断标准尽量是用影片带给我的情绪效应或是美学,多于片子的故事本身。短片像是开启一宗调查,当我们对一个项目有兴趣,我们就会进行调查,去查出谁是导演、编剧、制片,短片就是一个调查的元素,让我们可以做出是否合作的结论。我们也很少遇到看完了短片,就决定要做长片,短片通常只是一个调查元素。不过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例如最近与一个中国导演的合作,四年前他获得短片金棕榈奖,两年前在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又获奖,我们看了他两部短片,就下了做长片的决定,刚刚提到的澳洲导演也是个例子。
另一个是在法国工作的西班牙导演,他拍了三部二十五分钟的短片,我觉得二十五分钟这个片长是比较可以评断导演的才华,看他能不能撑起这二十五分钟。我们的评断依据是导演场面调度的功力,不是片子的主题、概念。因为有些杰出的短片,很有趣、很精简,但靠的只是一个概念,但是之后要走到长片,必须要评断导演的能力,是否可以用影像或人物让我们印象深刻。
Q:如果一部电影想要进入国际市场,你会建议在哪个阶段开始跟国际资方联系呢?另外,在接触国际资方时,新导演和资深导演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文森特·马拉瓦尔 :国际发行会因为导演不同,而有不同的阶段,比如像是侯孝贤导演,那是出于我们希望跟他合作,所以只需要他的一个概念,不一定需要剧本,我们就可以谈好下一部片要合作。如果是新锐导演的话,我们通常就会要求看他的短片作品,与他进行讨论、看剧本,尤其需要有当地的制片,提出符合在地可行性的财务计划。我们也可能因为喜欢某部电影,而发行已经拍摄完成的影片,但我们就不介入这部片的财务,单纯做国际市场的销售代表。
Q:你的意思是说,越早跟国际资方开启对话,对一个影片未来的旅程是有帮助的吗?
文森特·马拉瓦尔 :要看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会是相反的。每一家公司的做法不一样,在Wild Bunch多半是我们主动去找导演,例如我们会去看短片、剧本或制作工作坊,我们很早就会知道一些业界正在进行的计划。我们多半是主动寻找,而非被动。若是要我来估算,我们的片子有90%是我们主动找来的,单纯收到计划而合作的很少。
Q:数字化时代,电影制作量变得非常大,报名电影节也变得容易,当我们去报名电影节的时候,请问你有什么建议可以让自己的作品更为突出,不被淹没在片海之中?
文森特·马拉瓦尔 :一部电影有不同的制作阶段,到了参加国际电影节的阶段,就代表这部电影已经制作完成。我们介入电影作品的时间点可以是在剧本写作期、可以是有二十分钟或一小时试看片时期、也可以是作品完成时期,但是讲到国际电影节,就代表片子完成了。到了这个时候,选择电影的准则非常简单,就是要挑最好的作品。当电影完成了,在电影节里就没有特权。的确有些电影节非常具有实验性,但是他们大致上还是会选择最好的作品,很少会忽略掉品质好的电影,所以当影片完成了,唯一挑选标准就是品质。
Q:对于新导演在选择报名的电影节上有没有建议,比如哪些电影节可能对于亚洲电影或新导演的电影会比较有兴趣?
文森特·马拉瓦尔 :国际电影节有好几个不同的类别,有世界性的A级国际电影节,像是戛纳、柏林、威尼斯、多伦多、圣丹斯等,也有一些比较地区性的电影节。
现在电影产业有非常的好的一点:即使在东京、鹿特丹或莫斯科这些知名度相对较低的电影节中,如果放映了一部很棒的电影,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信息传播非常快速,所有人包括记者、圈内人、国际销售都会知道。一部尚未发行的印尼片,某天在五十个人面前做内部放映,三天后我就会收到当地发行写信给我,跟我说电影有多好看,要我赶快去了解,资讯很快就会传开。A级国际电影节当然曝光度最高,受众群最大,但在今日,我觉得有必要去试试有国际媒体、国际发行参与的其他电影节,因为接下来信息会自己传播。
Q:关于报名电影节,直接上网投递影片或找国际资方代理报名,相较之下会有差别吗?
文森特·马拉瓦尔 :两种方式都可以去尝试。大部分规模比较大的电影节,都在各个地区有协助选片的联络人,有国际发行商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可以帮忙后续包括线上注册、寄DVD的工作。以戛纳电影节为例,国际电影节的选片团队大约会有十五人,一步一步筛选片子,最后进入选片委员会,所以拥有国际发行商的好处是他们通常知道要把片子给谁看,电影节的问题从来不是选了不好的片,而是因为片子给了不对的人看,而错过了一部好片。当然如果因为给不对的人看片,而错失了戛纳的机会,还是有威尼斯、多伦多、圣塞巴斯汀电影节,如果是一部好电影,不太可能不被发现。有国际发行的好处是,当片子送出去之后,他可以主导这部电影的旅程。
Q:如果想要寻求国际合制或国际资金的投资,有什么机会或渠道吗?
文森特·马拉瓦尔 :我们说到合制,是电影尚未拍摄,仍在剧本阶段的情况下。现今有非常多的创投工作坊,例如戛纳电影节电影基金会就有举办,柏林、香港、鹿特丹等等也有。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电影市场展,全世界的国际发行与买片部门都会派他们的联络人过来看这些计划,所以我觉得最好切入的方式是,一开始去注册那些拥有选片小组的创投工作坊,很多片子都是通过这些工作坊得已完成,再来就取决于导演本身的资历,如果是拍过短片的年轻导演,就可以直接把短片寄给国际发行公司,以获得合制机会。
我们也有做过一些从短片发展成长片的合制,这些短片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发掘出来的,不一定是寄来给我们的。最近我们有两个正在进行的制作,来自澳洲及中国,都是导演的第一部长片,缘自于我们在戛纳电影节看到的短片。总结来说,进入国际合制市场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拥有选片委员会的创投工作坊。
Q:曾听一位国际发行说过,他挑片通常会给剧情片五分钟、纪录片十分钟的机会。你的挑片原则是什么呢?
文森特·马拉瓦尔 :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比较喜欢花多一些时间。我们其实有非常明确的方向,我先说明这只是我们的做法,不是唯一真理,我们的做法类似美国人所说的「导演取向」,对我们来说,导演负责电影的完成,导演创造出一切。
举例来说,我们几乎没有发生过只因为剧本好,而不管导演是谁就决定合作,导演要建构出电影的小宇宙,所以他的贡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确我们比较少从创投计划中去挑影片,那种通常只有五分钟,必须非常有效率地在短时间抓住对方,留下印象,我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尤其美国电影常常这样做,但这不是我们的作法。我们会先跟导演或制片见面谈谈,或是看到喜欢的电影,我们就主动联络导演希望见面,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也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例如我不是很文学性的人,对于书写的作品没什么感觉,但如果我跟导演聊就比较能感受,也比较能泰然自若地对导演的想法发表意见。
我的同事也有比较文学性的,对他们而言,剧本代表核心价值,对我而言,剧本没有什么价值,我比较看重与导演的交流,或是看他的短片及过去的作品。对我来说,剧本只是个参考指标,好剧本可能拍出烂片,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不玩闪电约会这招,我们不会只花五分钟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然后给意见,我也不懂如何这样做。
Q:你同时担任片方和制片的角色,请问这两个角色有什么异同之处?
文森特·马拉瓦尔 :这样的角色历经演变,最初并不是如此。从国际销售与制作的历史来看,在视频平台出现之前,国际发行商是渐进地去跨足电影制作,比如哈维·温斯坦、马丁·斯科塞斯的制片Graham King,他一开始是担任国际销售与发行,后来才一步一步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
随着电影产业的变化与视频平台的兴起,现今这样的角色要不是在平台底下工作,要不就是因为市场变得太复杂,而不再处理国际发行,像我们这样身兼国际发行与制片的角色,可说是一种幸存者。现在的国际发行商大多属于某家非本业的公司,例如Pathé、StudioCanal、TF1,它们的本业是电视台;至于独立的国际资方、或是从国际销售跨足制作的公司就比较少,例如Glen Basner创立的FilmNation、Wild Bunch、MadRiver,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但也所剩不多,因为市场的演变与平台的兴起,这样的角色有点被边缘化。
Wild Bunch的模式通常是我们喜欢某部片就去取得国际发行权,然后跟导演提议下一部片继续合作,同时也提出我们能提供给他的资源,例如我们跟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的合作方式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了《四月三周两天》非常喜欢,就跟他提议下一部片加入法国资金来合制,并且跟他分析法国电影工业的优势,最后我们合制了两部影片;与导演加斯帕·诺的合作,我们刚开始仅担任《不可撤销》的国际销售,最后也参与了制作。从担任导演的国际发行开始,再逐步转换成制片的角色,制片的工作是进入影片,与创作者一同讨论、滋养、发展,一部片的宣传周期通常有七、八个月,我们就从中建立起联系,慢慢地变成导演专属的对话人,之后就容易成为制片的角色。
Q:如果今天一个制片希望能往国际市场拓展、把影片推到国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文森特·马拉瓦尔 :如同我之前所提到的,想要打入国际市场,必须要先被看,不可能会突然打入国际市场,被看到的意思是说,国际制片看了电影,认为该作者有潜力、在国际市场上值得栽培。选择创投、电影节选片也都是一样的流程,一切皆始于被看到。
除了刚才提过的克里斯蒂安·蒙吉之外,另一个例子是乔治亚的年轻导演迪亚·库伦贝加什维利,她的影片《开始》在圣塞巴斯汀与多伦电影节夺得多座奖项,在此之前,她在国际影坛完全没有知名度,但是我们看到了她的两部短片,因此开始参与她的长片计划,在参展期间,我们逐步建立她的知名度,也让《开始》这部电影的发展非常成功,即将代表乔治亚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现在大家认识她了,我们就能预想下一部片可能参与合制的单位,他们也会对于有没有合作兴趣有些依据。如果今天是个尚未被国际市场发现的导演,在国际合制方面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
Q:《开始》这部片采取了非常节制、冷静的美学风格,请问这位乔治亚的女导演一开始就想要这么做吗?还是在制作的过程中Wild Bunch有给意见?另外这样的电影我相信在乔治亚本国是没有办法回收成本的,可以熟悉爱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以及现在海外回收的情况吗?
文森特·马拉瓦尔 :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时,我还没看到,但是我的一位合作伙伴先注意到并且表达想跟这位导演合作。至于她的风格,可能可以说是冷冽,场面调度手法令人想起《四月三周两天》。看到她在电影的处理,我们了解到眼前这位导演虽然年轻,但却能有精准的掌控,我们深深被吸引。我们从来不干涉她的电影风格,对制片团队也没有做任何要求,她的风格是非常个人的,是她想要做的,那是她说故事、拍电影的方式,不是技术团队里的某个人推荐或影响她这么做,她的团队是她自己组的。
这部电影的资金来自乔治亚、法国合制,剩下非常少部分来自其他各处的投资,成本不到一百万欧元,应该是在六十五万到九十万欧元之间,所以这部片预算很低。在剧本的阶段我们就决定合作,当然我们从她的短片看得出导演的调度能力纯熟,再加上她来自于乔治亚,我们会想在大银幕里看到乔治亚发生的种种,想认识这个国家、想看看那里的景色。不过要注意我们并不是旅行社,作品背后的创作者本身必须要有才华,她的风格是本身就具备的,不是我们制片方强加的。
下一步我们期望慢慢地打开国际销售,事实上这部片在全世界的销售状况还不错,不是说销售金额有多高,所谓的打开国际销售是指有没有让电影开启它在世界的旅程。当片子在全世界各地发行,我们可以期待她的下一部片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她会更有野心,她的导演职业生涯就此开始,所以我们的思维就是跟她发展关系,帮助她用适切的方法完整实践她的野心与愿景。
Q:近年来视频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好,对电影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你怎么看待视频平台?看到一个案子时,会先去思考这是属于视频平台或院线发行的案子吗?
文森特·马拉瓦尔 :我对于视频平台的出现保持着很正面的想法,它提供了额外的选择,开启了电影崭新且更有效率的发行模式,比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来发展的模式还要有效率。在视频平台兴起前,我做电影发行也二十多年了,过去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怒火青春》(La Haine),会遇到的问题是这部片的目标观众是年轻观众,但是这些观众不看有字幕的影片,所以只能在艺术电影院放映,我们很难接触所有观众,因为当地的发行商已经预设了电影的目标观众。时至今日,因为视频平台,我们有幸能够非常快速地接触到所有观众,观众也知道上面都有字幕,看看现在在Netflix上非常成功的就有土耳其片、波兰片等,我认为视频平台的出现提供了发行上的额外可能与选择,它并非带来问题。
以艺术层面而言,我不认为电影有「电影院放映」与「视频平台播放」的分别。如果这样去分类,Netflix的《罗马》(Roma)或《爱尔兰人》(The Irishman)其实比较属于影院放映型的,但视频平台上也有非常多的法国喜剧,固定每周三上档,它们没有任何艺术企图,比较像是以前定义下的电视电影。所以我认为到今天,当我们看完一部片,从艺术性的角度,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断定这部电影是拍给影院或平台放映的,会有这种区别多半是出于经济的角度。
现在视频平台在部分国家已经培养出它自己的观众,当然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同,例如欧洲的观影群比较年长、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观影群比较年轻,所以状况变得复杂很多,很难区分。也是因为如此,我乐观地欢迎视频平台,它让每个国家有更多机会去思考,如何依据各个影片的独特性,尽可能有效率地达成其设定的目标。对我来说,这个区分是经济性的、不是艺术性的,也就是说一部片在财务脉络下,比较适合平台还是影院播放。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开始》,在某些国家我们卖到MUBI上架,MUBI是个专放艺术片的视频平台,但在其他国家我们就通过一般的发行模式,在影院上片。平台的来临开启了全新的可能,让我们接触新的观众群,但是与艺术性无关,而是经济上的理由。
Q:如果中国创作者有一个案子要给你看的话,你会希望在片子里看到什么样的亚洲特色?
文森特·马拉瓦尔 :我们不会把电影依照它的产地而有不同的欣赏标准,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品质,品质是指这个团队是否有足够的工作热情。电影其实就是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热情,你想跟片子共同开启一段旅程的能量大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感受到团队想要分享与这部电影共同闯荡的渴望,所以我们是否收下一部电影,取决于眼前这个团队的品质与应对,不论是亚洲、拉丁美洲、美国、法国都一样。
送到我们面前的计划书常常是爆掉的,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处理,其实寄计划书给我们是没什么用的,我们的买片与卖片部门每天收到五、六个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剧本,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完的,所以像我之前说的,你必须让自己被看到,不管是工作坊、市场展、还是第一部或第二部长片都可以。在信箱收到你的计划、然后打开阅读、最后决定跟你合作——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也相信全世界大部分的制片,在实际读任何东西之前,会先去查创作者的背景、拍过什么片,而这些信息往往也是通过市场去取得。
Q:请问目前华语片相较于其他的亚洲片,在国际宣发上是比较容易的吗?华语片在国际销售上有没有什么改变的趋势?
文森特·马拉瓦尔 :我不认为当今的观众会用电影出产国来挑片,观众选片是因为他想看,这个想看的心情是由很多曝光建立出来的,可能是口碑、媒体宣传、电影节、影片主题或电影海报、预告片、剧照等等。我们身为国际发行的工作就是创造曝光,并且加乘这些曝光,尽可能卖力地让大众觉得越受吸引越好,所以跟出产国家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我不喜欢「浪潮」这个字,因为会跟法国电影其中一段历史有连结,但过去是有过一些潮流或趋势,例如有一段时间大概持续四、五年,大众非常钟情于罗马尼亚的电影,他们可能对罗马尼亚的电影比较好奇,而不是斯洛维尼亚,当时有股热潮,差不多在同一段时间,有四、五个罗马尼亚导演拍出国际观众喜爱的电影,墨西哥片、韩国惊悚片热潮也是一样。但是当我销售一部意大利片或巴西片时,对方从来就不会说「对!我们就是在找巴西片」,不是这样运作的,大家要找的是好片。
至于说到华语片,我认为中国电影工业建立与兴起,让越来越多有才华的导演出现。最近这四、五年我们的确发行了不少华语片,不是我们刻意想要,而是中国新导演拍了非常多出色的首部电影,或许也是因为有电影工业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实践视觉上的野心。例如我们发行了《暴雪将至》,是董越导演的第一部片,电影中的场面调度令人印象深刻,我没有看过任何法国新导演的第一部片带来过同等的视觉冲击。我们也做了《春江水暖》,这部片入选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也是中国片。
做中国片或华语片并不是出于我们的决定,我们所寻找的就是优秀的才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如果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更好,因为对全世界的观众而言,去看外语片的诱因之一就是异国情调,发现不同的文化,就像在其中旅游一般。如果现在有位北欧原住民拉普兰的创作者,我们就会想说从来没有在大银幕看过那里的景色,就会比在法国拍摄的电影还感兴趣,能让观众在电影中未曾出现过的场域一同旅行是很重要的层面,这也是让人感兴趣的因素之一,所以在我们的发行或合作目录里,有不同的国家比较好。我们仍与张艺谋、王家卫这个世代的导演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新一辈的中国导演出现,他们的华语片能够以不同的类型满足观众,也能在国际观众间引起回响。
Q:有些发行难度比较高的电影像是《阿黛尔的生活》它是一部三小时的女同志片,黑白片《艺术家》(The Artist)等,经过Wild Bunch的规划后,这些电影的成果都很好。电影里的哪种特色会吸引你去代理或投资它?
文森特·马拉瓦尔 :视频平台让我们体会到过往认为主题艰涩、很难推的影片,其实不尽然如此。我认为传统发行的模式渐渐地让我们变保守、自我设限,认为某些片很难发行,我不相信这样,我觉得观众其实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奇,像刚提到土耳其片、波兰片,没有人想过它们会在Netflix达到全世界三百万的观看人次,我觉得观众的好奇心程度是完全被传统发行方式所低估。传统发行的思维在取悦主流,而忽略尝试去接近广大的少数族群,如果影院有两百五十个座位数,传统发行只会想办法去把它塞满,而不会想到要去尝试一千人的影院。
我们发行一部片子宣传资源没有大片商那么多,所以由我们发行的片子,必须本身就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例如我可以说「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影需要让我们感到惊喜,本身就要有宣传点。例如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的影片《育蝇奇谭》,故事是两个废柴决定要训练苍蝇的故事,简单一句话就能引起兴趣,大众听到会很惊奇,想要去看;如果今天改成超级英雄要去拯救地球,我就不确定是否会引起观众相同的兴趣。在创投提案的时候,常常就有些比较吸引人的案子会跳出来,我们选片也是试着选出具有强烈辨识度特质的影片,它们才能在宣传上与比较商业的影片区隔开来。
Q:能否请你分享跟王家卫、是枝裕和合作的契机、模式或是趣闻?
文森特·马拉瓦尔 :Wild Bunch创办人之一Alain de la Mata,当时他在英国发行亚洲片,有个公司叫做M.I.H.K.,来自香港制造的英文Made in Hong Kong,他算是最早将王家卫引进欧洲的,早在《重庆森林》之前,所以我们跟王家卫算是有些渊源,是他的粉丝,同时也有在欧洲发行他的电影版权的经验。后来我们看完《重庆森林》,我就主动联络想跟他合作接下来的电影,但他当时已经跟法国制片Éric Heumann合作,后来他们也合作了《花样年华》与《2046》。每次我想问他有没有意愿跟我们合作,他都已经有国际制片了,在《2046》之后,这位制片关闭了他的公司,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跟他讨论计划。在合作《一代宗师》之前,我们讨论非常多的合作构想,包括尚未问世的《来自上海的女人》(The Lady from Shanghai)等剧本。最后我们终于合作了《一代宗师》,整个经验很好,可能因为我们算是很会找资金,他也需要国际合作伙伴,我们互相欣赏,他也知道我很喜欢他的片,一切算是水到渠成。
王家卫的工作方式是相当独特的,他在一部片会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想法,例如《花样年华》一开始只写好最后一场戏,然后才慢慢发展剩下的故事;他会汲取之前的作品,一点一滴地衍生出新的作品。他不是先写好剧本、拍摄、剪接这样传统的模式,他先拍一点、再剪一点,再拍、再剪,然后重改剧本,再拍、再剪。他的创作过程跟传统电影制作完全相异,整个过程是漫长、必须要有热情、要有心理准备需要等待,为什么他会一再重新拍摄与剪接?因为他看到剪接不完美的地方就会想要修改,就需要回到现场再重拍,这就是他身为完美主义者创作的方式。
跟是枝裕和的合作就比较传统,我们从他的第三部长片、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距离》(Distance)开始合作,这部片的国际销售并不理想,我们没有办法把片子推出去。我就自我安慰,告诉自己这就是一次失败,我就没有再去追他接下来的片子。多年后,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片子《奇迹》制片来电,问我有没有兴趣接下这部片的国际发行,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是枝裕和,他们主动来找我,减轻了我当年《距离》卖不好的羞愧感。于是我接下《奇迹》,后来也卖得不错。
《奇迹》倒是有个小趣事,这部片创下我个人最短的旅行纪录,他们要我过去看片,我出门,早上六点降落东京,十点看片,下午两点搭上回程班机,仅仅为了看片,飞到东京半天,因为我想要表现对导演的崇敬,所以愿意安排这样的闪电旅程。后来的《如父如子》(Like Father, Like Son),他们让我们加入剪接的讨论,他们给我们看剪接,想了解电影里的日本文化元素是否能被西方人所理解、会不会造成困惑。
《如父如子》的合作也非常成功,于是我们就以这样的模式继续合作,到了《小偷家族》(Shoplifters),他们会希望我们对剧本与剪接注记想法,可以看出来我们开始慢慢地发展出一种关系,他们需要我们提供来自西方的看法,为了确认日本文化的细腻处能被理解、不会造成困惑,我们合作过程的互动性越来越高。他最新的电影《真相》(The Truth)因为是在法国拍摄,所以在他们要求之下,我们的角色更为吃重,需要在很多层面支援。是枝裕和也变成我们合作导演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很爱慕尊敬他。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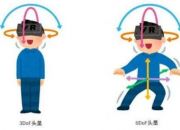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