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与改革开放同龄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走过了四十年,现在要在新的媒介环境和时代语境下谋求更大发展,恰逢其时。互联网新媒体语境下电影批评“何为”?又该“如何为”?
“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我们还能做什么?
进入互联网时代,对电影批评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时代”。文艺批评的“别车杜”时代,就是那个俄国文艺批评的黄金时代,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为代表的时代,似乎是一去难再返了。
这是一个“人人都是评论家”的时代。但我们依然要坚持“发声”、“发言”,虽然不能一呼百应,哪怕我们的声音飘散在互联网的大漠中。在当下多媒介众声喧哗的汹汹舆情中,无论是学院派、专业影评,迷影观众影评,或者仅仅是一个朋友圈的一个点赞、一次议论,豆瓣、猫眼的一次打分,微博、微信上的一段感想、评论,都是电影最终舆情、口碑评价成型的源头之一,都是无数蝴蝶的一次次震动!都肯定会影响到票房的走势和高低。
今天专业影评失去“轰动效应”实际上并非一日之寒,这与电影本身生产创作的实际,电影的工业生产特性,电影的综合艺术、集体生产特性都有关系,并不稀奇也不必哀叹。电影导演主创与电影评论者的关系,如与文学界比,它与诗人和诗评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诗人和诗评家之间可能确立起很好个人的友谊关系,他们可以在圈子里吟诵点评唱和应酬,但是电影导演和评论家之间不一定能够确立这样的关系。就像我这几年电影工业美学思考的那样,导演在电影中的地位降低了,电影不是导演个人的工作,电影是一种工业,电影有很长的时间链条,是一个“长尾”,需要很多工种来协同完成。评论家对于电影的评论,都是在电影上映之后,创作者很难马上就吸收,无法去修改。而且有些电影的修改权,几乎不在导演手上。
但这样是不是就能说影评没有意义呢?非也。影评,包括专业影评、网络影评,各种点赞、议论、打分、评选,都对观众影响是很大的,对导演、编剧主创等,也有间接的影响。只要他还想继续做电影。而这种汇合而成的影片舆情、口碑评价,对观众的影响是很大的。观众对观片的选择,对影片的进一步评价,又进一步直接影响到票房,尤其是在一个“新口碑时代”。
新口碑时代,专业影评其实功不可没
今天做广义的影评的人很多,有专业的,有非专业的,有群众、粉丝、影迷,也有普通网民。我在北京大学的老师谢冕先生,常说作为批评家,无论如何,要“发言”,要“发声”。这几年我在北大鼓励学生利用新媒体发言、发声,只要发言就是在表明我们的立场,就是宣示我们的存在。在电影课上,我要求同学们写微影评,120字的微影评,每人每个学期至少20篇,算平时成绩。这些同学听我讲课,看我们的专业文章,这些专业素养转化为网络化的一二百字的短评。我还鼓励他们海量地发布到他们的朋友圈,发布到他们的微博上去,鼓励三百个学生互相转发,一个学期下来就是6000多篇微影评。这不也是在做影评的工作吗?虽然不一定很专业,但却成为电影舆情口碑重要的一环。
当下的影评生态就是一种众声喧哗。有专业的,有半专业的,有非专业的,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长尾“的知识生产的体系和机制。我们最后对一部影片的评价的形成,就是由大量不同形态的影评一环一环互动最后形成的,这是一个类似于蝴蝶翅膀的振动效应,我们专业影评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一个缺之不可的环节。
所以我们既没法自以为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我曾经提出“新口碑时代”的术语,意为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口碑和票房严重不一致,甚至成反比的时代。那个时候,资本过剩,资本提前买票房、提前锁定场次,有些偶像的粉丝们都主动筹资预定某部电影的放映场次,有些电影还说自己是“负口碑”营销,不惜自我作贱而引起舆论关注。但在“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内容为王、品质为王,费尽心机的“水军”的工作,充其量只是沧海一粟。资本、“水军”可能影响前几天的“口碑”,影响前几天的票房排名和排片,但决定不了更远。我们的观众逐渐成长起来,审美水准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专业。这样的一个新口碑时代,最后形成的口碑,我们是可以信任的。互联网时代,网民,只有网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因此,现在越来越进入了一个真正经过各种舆论传播和生产机制最后形成口碑的“新口碑时代”。与质量基本平行一致的口碑最终决定影响排片、票房。在舆情口碑形成的过程中,无论专业影评还是非专业影评,都功不可没。专业影评对网民大众影评无疑具有某种示范和引领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无法量化计算。
我们如何总结“钟惦棐经验”?如何从钟惦棐“接着讲”?
在钟老家乡江津的一次会上,我提出中国电影评论、中国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学派的“钟惦棐经验“的课题。最近就在考虑写这篇文章。我觉得钟老很多思想和成果,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也非常有用,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虽说现在评论的形态多样化,传播方式也非常复杂多样,但批评的精神是连贯的、不变的。批评的接受对象,那种最广泛的读者、观众也是不变的。当然,今天影评读者、电影观众的年龄、知识学养、思维和想象力方式等方面则是与时俱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钟惦棐先生的文章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扎根大地、务实实际,敢说真话、尖锐深刻,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包括中国传统的文论都转化为了自己的血肉,他的影评是真正“信、达、雅”的,真正重视电影观众也尊重影评读者的,他有时苦口婆心,常常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而且都不是长篇大论,没有套话,没有不接地气的抽象玄虚的理论,一句话,通俗浅近、语调活泼,有时还有点幽默谐趣,有时暗含讥讽,甚至可以说非常适合于今天的网络传播。这是值得我们今天专业影评工作者学习的。钟先生就和美学界的宗白华先生一样值得总结,我写过《论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宗白华经验》,现在我们应该总结“钟惦棐经验”,把他们的本土化立场、中国化叙述,尊重“常人”、普通人观众的精神、经验运用到我们今天影评的专业性建设中。
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与批评是什么关系?
一般认为,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是“二元对立”的。但理论与批评也形成一种二元对立关系。理论和批评不一样,理论是一种建构,一种体系性的构建,是从本体出发经由各个维度展开的一种体系建构。它也是对中西文化、中西思维,各个媒介、学科的跨越。但批评是一种实践,是理论的具体运用。现在我们不像八十年代了,那时候我们的前辈学人,包括今天依然活跃在第一线的很多评论界前辈,他们从西方理论中借用了有效的武器,对当时很多新出现的中国电影现象,找到了阐释、解读的话语,别开生面,让我们有豁然开朗之感。
但到今天,中西文化的关系、中西理论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包括中国电影产业自身发展的状况,都使得很少有理论能够像八十年代那样拿来就可以用。彼时我们是长久封闭之后的突然放开,长期荒芜之后的突然繁盛,但现在我们已经循序渐进,已经交流、流通、实践、本土化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运用西方的理论,不应该是食洋不化、生吞活剥式的。
评论一定要言之有物,一定要有明确的对象,不能悬空,对象要具体、评价要务实。我认为,理论和评论最好构成这样一种辩证、互补互动的关系,评论者经长期学习养成理论素养,善于理论思考,具备一定的专业性。他们关注现实,努力去发现现实中的问题,继而以综合汇通的理论,以综合思考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现象,甚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某些理论、原则。但理论必须回到现实中去,通过运用再反过来修正和矫正理论建构。电影评论者要有一种架构中国电影理论学派的主体性,是用自己的主体立场、主动去同化和顺应,既同化又顺应。
也就是说,批评实践不应该理论先行,不是带着理论框框去寻找例证,不是“骑驴找驴”。不能固守某些理论教条。理论是开放的,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批评对象应该是从现实中来,经过理论总结又回到现实中去。批评者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在现实中发现问题,然后寻求理论的依托,要力求思想的深度和力度,然后又回到现实中去进行批评实践和检验,再回过来继续进行理论思考和建构,甚至是理论的体系性建构。
近年我提出的“电影工业美学”与“想象力消费”理论,都是因为在现实当中发现了问题。“电影工业美学”是觉得有些导演极端蔑视电影的工业化或在工业和美学之间寻找平衡,而电影仅仅强调工业化又远远不够。“想象力消费”的提出是强烈有感于中国电影长期缺乏想象力,科幻电影一直不发达。正是有感于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形成了一些理论思考。令人欣慰的是,以“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费”为理论视域或批评框架,能够对某些具体作品和现象进行比较有效的分析。无疑,电影的批评实践是一种理论的检验,通过这种学术话语的运用,留其有效,弃其无效,理论又能有所调整、有所提高。这是一个不断反转、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这是我认为的理想的理论与批评的辩证学理关系——既“二元对立”,又超越“二元对立”。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根据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年会上的发言整理)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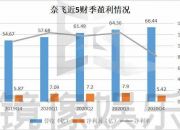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