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为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写一段先锋戏剧式的个人独白,大概会是这样的:“我,安德烈·阿尔谢尼耶维奇·塔尔科夫斯基,阿尔谢尼和玛利亚的儿子,玛琳娜的哥哥,伊尔玛和拉丽莎的丈夫,小阿尔谢尼和小安德烈的父亲。我生在苏联,死在法国;我是7部半电影的导演和一本书的作者。我是几十部影片和几十部书的主角,我被几百个导演致敬,我的影片被几千个电影节放映,被几万名学者研究,被几十万影评人评论,被几百万影迷热爱着并热爱下去。”
独白还可以继续写下去,比如“被几千万个文艺青年当成接头暗号”或者“被中国影迷亲切地称为电影艺术的‘圣三位一体’之一”等等。虽然不免有些嘲讽,但塔尔科夫斯基,或者按中文迷影圈说法叫“老塔”,确凿无疑地是电影艺术的某种至高标准,以至于形成了全球迷影文化中的一种值得拿出来讨论的现象。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又译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名导演,代表作有《镜子》《乡愁》《牺牲》等,被称为“电影诗人“。
在中文语境中,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可谓是某种迷影圈的“基本教养”。以豆瓣为例,塔氏的7部长片和毕业短片均有超过万人标记看过,其中近4万人“看过”的《乡愁》(1983)以9.1的高分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镜子》(1975)和《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也都高达9.0分。开个玩笑,塔尔科夫斯基可能是在豆瓣除了诺兰之外最受好评的导演(两人的作品也都因此而收获了不少一星差评)。而豆瓣网友的选择与堪称某种迷影风向标的《画面与音响》(又译“视与听”)杂志的影史百佳评选颇为相符。这份榜单每10年更新一次,2012年由846位影评人和策展人投出的结果中,塔氏的《镜子》位列19,《安德烈·卢布廖夫》位列26,《潜行者》位列29;由358位世界知名导演投出的结果中,上述三部影片分列第9、第13和第30名,塔氏也被同行选为影史十大导演的第五名。
简言之,塔尔科夫斯基在中文迷影圈,是某种接近于“不言自明”的伟大导演的存在。对这种神话地位稍加考察就能发现一些甚为有趣的历史路径,由此还可以反观内地迷影文化,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迷影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
一、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伊万的童年》
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最早传入中国内地,是作为“解冻电影”之一的《伊万的童年》(1962)被作为“内参片”供当时的电影界内部学习和批判。彼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一批“解冻电影”的名作如《雁南飞》《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等,被批判为宣扬“战争残酷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伊万的童年》也名列其中。虽然被批判,但“解冻电影”高超的艺术成就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成了彼时正在学习电影的“第四代”导演们日后执导那一批“伤痕电影”时最为倚重的思想资源。当然其间细节和逻辑十分复杂,只消提一个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例子就可见一斑:《小兵张嘎》(1963)正是中国电影界对《伊万的童年》的回应,其论据之一就是里面那个著名的翻墙过屋的长镜头;而且我也猜想(未经证实)《闪闪的红星》(1974)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是塑造“小英雄”上)也可以续进这个脉络。当然有大量的影片都在致敬《伊万的童年》,随手举两个例子就是张大磊的《八月》(2016)和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荒野猎人》(2015),前者的梦境处理非常相似,而后者更是直接照搬了不少构图和布景(如《伊万》中战争废墟和《荒野》中村落废墟等)。

《伊万的童年》海报。
塔尔科夫斯基接下来再出现在中国电影界的视野里,除去尚待考证的内参片和内部参考资料的介绍,还要等到1984年《世界电影》对《乡愁》(1980年代译名为《怀乡》)的介绍,随即在1986年9月的瑞典电影回顾展上,刚刚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牺牲》以内部放映的形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1987年3月的苏联电影回顾展上则放映了《安德烈·卢布廖夫》(当时译名为《安德烈依·鲁勃廖夫》,分上下集放映)。虽然1980年代的电影周仅在几个大城市放映,对普通观众影响有限,但对电影界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时至今日,如笔者导师郑洞天教授还时常津津乐道当年看到如《皮罗斯马尼》(1972,当时译名《比洛斯马尼》)和《长别离》(1961)时的“震惊体验”。而这些回顾展不期然的功能则是经由对电影界“世界想象”和“艺术电影观念”的形塑,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的电影创作,并通过学术著作进而框定了互联网迷影文化的经典谱系。在此需要提到的是几部著作:北京电影学院的影片精读教材《通向电影圣殿》(王迪等,戴锦华、崔子恩参编)、电影史教材《外国电影史》(郑亚玲、胡滨),以及邵牧君的《西方电影史概论》,这些著作和当时极为有限的外国电影著作的译本(如萨杜尔和格雷戈尔的电影史著作),构成了资讯贫乏时代电影爱好者们视野的天际线。
那么塔尔科夫斯基的位置又如何呢?《通向电影圣殿》中专门有一篇分析了《安德烈·卢布廖夫》,《外国电影史》中仅提及了《伊万的童年》片名;真正花了大篇幅论述的还要数乌利希·格雷戈尔在《世界电影史(1960年以来)》中对塔氏专辟一节的盛赞(该书称《安》一片是“苏联战后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对塔尔科夫斯基的研究文章也散见于电影学的几本刊物,仅此而已。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二、从港台地区流入的电影书籍和音像制品
时间回到1993年,来自台湾的电影爱好者庄崧冽(庄仔)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事件却在历史的回溯中成为一件堪称改写了中文迷影圈历史的大事。当然如今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几经沉浮,也算是知名连锁品牌;但如今塔尔科夫斯基能位居中文迷影圈的至高无上地位,还真得感谢庄仔。庄仔带到内地来的台版书《雕刻时光》(1993初版,李泳泉、陈丽贵译,台北万象出版)不仅是他1997年开办的咖啡馆的“镇馆之宝”,也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和学生传阅翻印的对象,甚至可谓是“思想资源”。更不负责任但可能是某种真相的说法是,无论是咖啡馆还是塔尔科夫斯基,可能都要感谢台版译者的翻译,因为该书俄语原名直译不过是“捕捉时间”,历史的偶然则是台版译者选择从英译本转译,将“Sculpturing in time”译作“雕刻时光”。这四个字简直是小资情调和中产想象的直接图像化,十足地富有“格调”。细究起来,这里面还有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行构过程的独特逻辑,以及与“世纪末怀旧”相连接的、堪称“情感结构”的“怀旧”——这恐怕也是《乡愁》成为“神圣文本”的原因之一。
台版《雕刻时光》在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本。这里也岔开去了另一个脉络,凡译作“塔可夫斯基”的皆可溯源到此,因为在内地的电影学传统里,根据新华社的人名翻译表,是要译作“塔尔科夫斯基”的。仅这一点就足以梳理出一个经由台港转入内地的脉络。当然还可以去考证一下片名,比如现在通行的译名《乡愁》《飞向太空》其实均是台译。

《雕刻时光》,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译者:陈丽贵 李泳泉,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
这一波塔尔科夫斯基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路径,正如上文提及,“雕刻时光”“乡愁”“牺牲”“压路机与小提琴”这些译名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另一个不被感知却更为重要的脉络,则是与庄仔一路,从台湾和香港地区流入内地的电影书籍与音像制品,录像带,LD,VCD,再到后来大行其道甚至创下一番盛世的“9区DVD”。一面是十足市井的、以录像厅为场景的香港和好莱坞类型片;一面则是极为精英的,流传于电影学院、知识界的艺术电影。当然后者的“目录”仍要追溯到诸如电影回顾展和学术著作的片目,但此时更需要纳入的则是“电影节”的维度,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电影节成为了音像制品的主要参考渠道。等到互联网登临内地,迷影社区诸如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成形,“淘碟”成为了大城市青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彼时的报刊杂志,尤其电影期刊也都会辟出版面来刊登“本周/本月碟报”,甚至有专门的网站和《DVD导刊》这样的专注DVD资讯的媒体平台。这些盗版DVD最初大都翻印自港版台版,后来发展到翻印欧美版本、集合各版花絮、包装精美的“最佳收藏版”。这类故事和资料几本书都写不完,仅说塔尔科夫斯基,从风靡一时的“牛皮纸袋”时代就有VCD流传,后来历经D5、D9,“洗版”无数,套装合集自是不提,以《乡愁》为例,2010年由“威信”厂牌推出的所谓“全球最佳版本”是这样的:

“3D9精装终极收藏版”(编号ST-155):Disc 1《乡愁》意大利二区16:9宽屏数码修复版(全球最佳画质版本);Disc 2纪录片《雕刻时光》意大利二区全球仅有16:9宽屏版;Disc 3三部纪录片《塔可夫斯基的乡愁》《莫斯科挽歌》《塔可夫斯基生命中的某天》,来自英二区Artificial Eye发行的DVD "The Andrei Tarkovsky Companion"(塔可夫斯基的朋友们)
这个版本封套包装参考台版塔尔科夫斯基拍立得摄影集(缪斯出版,2008)设计,外封印有一章拍立得照片,有五种不同封面,内封则印有塔尔科夫斯基文章选段,并附赠3张明信片。盗版做到这个程度,大概正版也得自愧不如吧。如果这不是因为爱电影和爱塔尔科夫斯基,那还能是因为什么。
三、“圣三位一体”
中国影迷对塔尔科夫斯基的爱,最突出的表现大概就是大范围地传诵了“圣三位一体”这个说法,虽然塔尔科夫斯基名列伯格曼和费里尼之后(猜测是因为名字比较长,而不是江湖地位)。据magasa的考证,这个说法是“中文迷影圈的发明”,最早始见于费里尼自传《我是说谎者》(三联书店2000年版)的简介。虽然magasa认为这一说法使得“塔尔科夫斯基的地位在中文迷影圈内被大大提高了”,但从“中文迷影圈”的知识结构,也就是互联网之前的电影学术圈考察,塔尔科夫斯基的地位虽不至于登峰造极,但比肩伯格曼和费里尼还是足够的。这里自然还要引述来自伯格曼的“金句”:塔氏的电影“捕捉生命,一如倒影,一如梦境”,以及更加“商业互吹”的盛赞:“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仿佛是个奇迹,蓦然你发觉自己置身于一间房间门口,过去从未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给我。这房间,我一直都渴望能进去一窥堂奥,而他,却能够在其中行动自如游刃有余……”
随着《雕刻时光》的简体版出版以及电影学课程在各高校的普及,从2005年开始,关于塔尔科夫斯基的期刊和学位论文开始出现,并在2007至2010年间达到高峰。这可能与塔氏日记《时光中的时光》(周成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出版直接相关。与之同时,9区DVD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塔氏两部学生作品《杀手》(1956)和《今天不离去》(1959),以及一系列相关纪录片也有了资源和由网络字幕组翻译的中文字幕,也为这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
在各高校的教学中,塔尔科夫斯基也因为前文所述种种路径,成为了某种“艺术电影”的必备分析对象。分享一则笔者的亲身经历,在某年讲授《世界电影史》课程时,一位学生告诉我,她曾在六门不同的课上听过任课教师讲《乡愁》,并且不约而同地都是用“手持蜡烛走过水面”的那个10分钟长镜头举例子。虽说电影学院授课片例当然是与时俱进的,但对于一些“经典片例”,还是颇有传承性的。如果7门课都讲《乡愁》,那这个细节恰好说明了为何塔尔科夫斯基作为“电影大师”的“不言自明”之处:长镜头。

《乡愁》海报。
溯源起来,这还得追溯到张暖忻和李陀那篇著名的论文《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1979)。简言之,张暖忻等“第四代”导演以“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当然这是一种因为时代局限,但也或许有意的误读)来尝试突破彼时电影中僵化死板的“政治修辞学”的一次尝试。对整个中国电影界的深远影响自是本文无法讨论的,但必须指出其效果之一就是将“长镜头”建构为了一种“电影大师”的指标。这个标准又经由互联网扩散到中文迷影圈内部,时至今日,精心设计的“长镜头”仍是影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乡愁》里那个长镜头其实并非塔氏生平最高杰作,但它在着实地“神圣”之余又相对简单,“容易看出好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从学术界到迷影圈里塔氏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名场面”。
当然塔氏一生拍出过无数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的长镜头,首先要数《牺牲》结尾的“烧房子”,还有《伊万的童年》里的飞行梦,《安德烈·卢布廖夫》里的飞行、铸钟,《飞向太空》里的失重,以及《乡愁》里的自焚等。这些长镜头被无数导演反复揣摩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致敬,不说毕赣,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即“萨金塞夫”)2005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一鸣惊人的《回归》,结尾处两位少年那三次折返搬运,难道不是复现《乡愁》里那动人一幕吗?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和其父亲阿尔谢尼。
四、“塔尔科夫斯基作为方法”
塔尔科夫斯基在中文迷影圈最近的一轮传播,则与“慢电影”的兴起、电影节圈子的形成和更新一代导演的登场密切相关。用最简单的方式描述,2008年被提出的“慢电影”(slow cinema)是逐渐内卷化的电影学术界渴望已久的新概念,而这个概念被同样渴求新概念的国际电影节圈子立即热情拥抱,仅仅几年,电影节、评论界和学术界就已经勾画出了一套完整的谱系和框架。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个遍及全球的“电影节网络”已经形成。
到最近十年,影迷已经不再需要像互联网初年那样渴求资讯与片源,甚至不再需要淘碟,网络下载和在线点播足以看到绝大多数他们想看的电影;电影书籍更多了,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全球化的购物网络直接购买外版书和电子书,内地设立影视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出国留学也越来越容易,加上数码转型已经完成,家用级的数码相机甚至手机就能拍出高清影像,总之,学习电影甚至拍摄电影的成本变得更为低廉,“电影梦”不再是二三十年前那样遥不可及。当然,要进入“行业”可能还是非常艰难,但进入“电影节圈子”,并没有那么难。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讨论的是“塔尔科夫斯基作为方法”。为什么那么多导演,无论是内地的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都那么热衷于将塔尔科夫斯基作为形式和风格的资源?这当然与“如何想象艺术电影”有关,但更重要的,或许是与塔尔科夫斯基在全球性的迷影文化中的位置有关,与经由互联网的、自学院而大众的话语传播过程有关;而更实际的,可能是与国际电影节的圈子与选片口味有关。
这其中当然还要提到毕赣,在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潜行者》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带来的震撼。《路边野餐》(2015)和《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都是与塔尔科夫斯基的对话。毕赣在国际电影节和国内市场的成功可谓是在中文迷影圈再度推广了一次塔尔科夫斯基,最直接的效果之一是塔氏的日记被炒到高价,《雕刻时光》成了畅销书,甚至几本关于塔氏的学术著作都获得了被翻译出版的机会。
而放在全球范围里,毕赣甚至算不上是塔氏追随者里最成功的——除了前文提到的伊纳里图和兹维亚金采夫,最受电影节和评论界认可的还要数在戛纳获奖无数的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电影摄影上甚至早就有了“塔尔科夫斯基式/塔尔科夫斯基主义”一词,而塔氏发明的不少电影语言早已融会贯通在艺术乃至常规电影里了。你能发现乌尔善在《画皮II》(2012)里的飞升镜头其实是致敬塔尔科夫斯基的《牺牲》吗?

《牺牲》海报。
五、“文化英雄”
最后还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塔尔科夫斯基?难道仅仅是因为“雕刻时光”和“乡愁”这些译名足够美丽,足够高概念吗?十多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谈《雕刻时光》,当年的结论今天看来依然有效,甚至可以说是愈发有效。不妨摘抄在这里:
塔氏坎坷的一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饱受苏联“迫害”的天才导演,塔氏身上似乎天然的道义正确性,使得他或多或少地被用做中国导演和观众的某种自我投射(并且也是塔氏生前在冷战另一边的西方世界饱受赞誉的重要原因)。这应当是一个更为直接和内在的原因。天才如塔氏,一生竟只有“七部半”电影传世,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在后冷战语境下,不得不说是一个极为完美的榜样。(写于2009年2月)
换句话说,塔尔科夫斯基就是一个“文化英雄”。中文迷影圈对塔氏的尊崇,几乎可以称作是一种“情结”或是“综合征”。影迷们渴望伟大,因为他们想超越琐屑和平庸。话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如果你还爱老塔,那就多看看他的影片,再读读他的著作和传记,以及明年将是他诞辰90周年,按照国内电影节的习俗,逢五逢十都有纪念影展,那就准备抢票去看大银幕吧。
作者:王垚(电影学者,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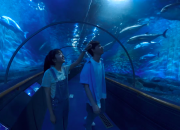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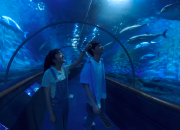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